今年10月1日是上海中华艺术宫对外开放五周年,作为纪念中华艺术宫五周年的大展之一,上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海山水画展“文心雕龙——上海山水画邀请展”于9月17日到10月7日在中华艺术宫0米层三大主展厅对外展出。
此次展览由中华艺术宫主办、澎湃新闻协办,参展画家从1920年代出生到1980年代出生的三代画家总计50余人,参展作品120余件,其中既有煌煌山水巨制,也有即兴写生之作与见出文人雅兴的山水手卷与册页。
此次展览的全部作品结集并已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刊发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顾村言为展览所撰写的代序《重估上海当代山水画创作的意义与思考》。
在当下中国,上海当代山水画乃至中国画的创作被低估久矣。
追溯原因,牵涉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态乃至艺术市场的变迁,也牵涉到百年来因外来冲击导致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承的艰难与曲折,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先后影响下中国画价值判断体系的紊乱,涉及的话题之广大之复杂其实远非艺术这么简单,也远非一篇小文可以讨论。
然而,如果从一个更广的历史语境看待当下上海当代山水画的创作,无论从真正传承中国文化精神或是深入中国画的内核来说,抑或从对中国画真正的创新精神而言,对上海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创作的真正实力都极有重估的必要。
这来自于上海这座城市内在的巨大文化实力与底气,也来自于宋以来中国文化南迁后,江南这片土地强大的中国文化基因与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正思考中国画的未来乃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梳理上海当代中国画传承教育、创作现状中的不少话题,无疑都值得探讨与反思,也对下一个百年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画的发展不无启示。上海中国画的文脉延续或隐或显一直是清晰的。当代上海山水画实力名家的出现,既有赖于上海开埠至今对中国艺术的灯灯相传,也得益于上海这样一个极具开放性城市的巨大视野与吸纳能力。
 陈佩秋作品
陈佩秋作品在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巨大精神力量与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的当下,回看中国绘画,经过百年多来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巨大转折,确实也到了重新审视与梳理的时候,而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最大策源地,重新回看与重估也因之有了巨大的思想与社会意义,尤其是山水画,因其承载的思想性与丰富的技法性,也因其隐逸情怀对于主题性创作的疏离,加上上海这一城市的文化积淀与大境界、大视野,中国画的真正文脉与精华不仅在上海保留得最完整,其开放性与真正的创新性在中国也同样走在前列,然而所有这些在相当长时间其实是被遮蔽的,至少并未被真正的系统梳理。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由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主办、澎湃新闻协办的“文心雕龙——上海山水画邀请大展”与这本《上海当代山水画作品集》其实只是一个起步。
由于时间的原因,此次大展邀请的上海山水画家难免有疏漏处,展览作品的组织也不无仓促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上海二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山水画大展,这次大展也是一个真实的纪录,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画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画家,三代人的笔墨与心中的家山,不仅是百年来中国山水画跌跌撞撞回环往复一路走来的鲜活见证,也承载了中国画前辈大家到当代上海画家对中国画与中国文化的诸多思考与期望。
(一)
回到此次展览的总标题“文心雕龙”,选定这一主题的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先生说是受“文心游艺”展览启示的神来之笔,这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对中国绘画长期深层次思考后的妙手偶得——作为一个系列大展,这一立意就当下的语境,不仅准确贴切,更有一种高远之境界。
这样的标题其实切中了百年来对中国画内核问题与当下现状的的一些真诚思考,也是回到中国绘画的目标与功用等重大问题上的思考与定位——中国画的话题从来就并不仅仅是绘画的话题,而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话题。
中国画该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画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如果简单回答,孔子的“依于仁,游于艺”或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可算是答案。《文心雕龙·原道》记有”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原本用于文论的此语用之于绘画,并无任何不妥处。正如宋代邓椿《画继》提出的“画者,文之极”,中国绘画的主流至少从北宋以后就是文人化的艺术,即所谓文人画,“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了庐作品
了庐作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目标,正在观照与解决天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生命中最鲜活的所在,此即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时所说的“吾与点也”的要义所在,从这一角度,中国绘画之所以呈现出与西方绘画完全不同的路径,也正在于从一开始就是致力于“道”的认知,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或谓一种诗性的探寻,同样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并不仅仅是技之层面的话题——当然,技却又是一个基础。
目前可见的汉画像石及大量写意性的汉魏壁画砖画已可见出这一特点,而山水画则初步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与宗炳的《画山水序》都是重要的文论,宗炳对山水画阐明了其虚静情怀和畅神功能,并以“澄怀味象”、“神超理得”、“闲居理气”言山水画欣赏及其心态,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虽然当时及其后唐宋绘画也同样承担了宏大叙事的需要,如皇家贵族与庙宇道观的装饰。
 萧海春作品
萧海春作品由唐而至宋代,被董其昌认为是南宗之祖的王维之画真迹渺不可见,五代时期善画江南真山的董源以平淡天真开中国山水画的南宗之美,中国绘画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到宋代,更由于大量文人的参与,以画为寄,以画求道、证道,以画言志,几乎是宋代及其后中国画家对待绘画的主要态度,到元代,倪瓒揭示的“聊写胸中逸气”更是成为中国艺术的逸格,其后几乎成为中国绘画的最高标准。
 卢甫圣《翠微》
卢甫圣《翠微》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元代文人多求隐逸,山水画更是达到了中国书画与心性结合的一个高度,也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一个高峰。到明代,从“吴门”而至于上海的“松江”,以董其昌的出现更为中国山水画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层次意义的梳理,董其昌云:“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他的寄情书画,以画为禅,多以冲淡超逸为衣,表面是似乎是复古,然而骨子里却是真正的创新,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成为一代书画宗师辈人物,而本质上而言,董其昌却实在是一位中国文化精神的积极传承者。以他为代表的松江派提出的“南北宗论”与“直见心性”等至今影响而不衰,除了直承笔墨的“四王”一脉,也同样启示了注重自在天性的八大石涛。
陆俨少先生一直记得其师冯超然对他所说的话:“中国山水画自元明以后,流传有绪,不绝如缕,一条线代代相传,现在这条线挂到我……用功一点,有希望可以接着挂下去!”这句话的语境与明初方孝儒被杀时士人担忧的“读书种子绝矣”之意颇有相近处,不仅说明一种责任与使命,更在于“原道”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精神的灯灯相传。
然而,百年来中国社会遭遇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变化,此一灯灯相传在当下看来,不仅史无前例地艰难,更在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已然不同,或者可以说,在当下的“原道”,比之前人,更加困难,也更需要一种超人的勇气与毅力。
(二)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至少也是中西文化结合最好的城市,然而上海其实更是一座中国传统文脉底蕴极深的江南名城。
以书画而言,从上海这片地域最早可追溯及比王羲之还早的西晋《平复帖》,从慨叹“华亭鹤唳”的作者陆机一直到董其昌,再到晚清民国时期崛起的海派书画大师,上海一直是这些书画大师的故乡或优游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现代艺术发展如何眼花瞭乱,上海一直有这样一批人,或隐或显,接续着江南文化的精神谱系,守望属于中国文化的家园,对于中国书画笔墨的丰采姿神与自在天性,一直心有所会,备极珍视。
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缘于移民城市的特点、工商业与对外交流的繁荣以及文人画家在租界的避乱便利与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导致四方画家与文艺界精英纷纷麇集于此,以至于中国近现代艺术无不发源于上海。具体到海派书画的崛起,一开始或许并非接近中国艺术的本质,也正如1899年张祖翼跋吴观岱画作首提“海派”二字所评论的:“江南自海上互市以来,有所谓海派者,皆恶劣不可暂注目。”然而精英不断涌入的上海是何等样的大熔炉与大境界,这样一种被文人鄙夷的小“海派”不久即被一种更大气的大“海派”所代替,赵之谦、任伯年之后,可以吴昌硕先生的出现为代表,所谓“强其骨力墨淋漓”,其内在的大气与骨力、苍莽也启发了其后的齐白石、黄宾虹,在彼时国难不断的情况下,直抒性情的中国画逐渐成为维系提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其精神境界至今影响而不衰,无论是刘海粟、潘天寿等,无不受其润泽,上海一方面是坚守中国画文脉与笔墨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在开拓新境与吸收西方文明方面,同样显示出海纳百川的气度。
吴昌硕之后,民国时期海派的纷繁中,则以更大的气象对于东西方文明经典进行包容并蓄,流波影响而至于全国,江浙之外,北至北京,南至岭南皆在其列,正如郎绍君先生在分析海派时所言:“ 民国时期的海派,处在社会变革、西潮涌入、启蒙和救亡交织的环境中,有反叛有固守,有磨砺与创造,呈现出折中变异的新局面……如果把萧俊贤、金城、陈师曾、陈年、王梦白、叶浅予、蒋兆和视为单纯的北京画家,而无视他们与上海的渊源关系,就不可能对他们有全面和深入的认知。美术史需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画家。惟其如此,才能把握动态中的艺术现象。”事实上,除了定居上海的吴湖帆、刘海粟、林风眠、张大壮、陆俨少、贺天健、钱瘦铁等外,飘零海外的张大千、定居杭州的黄宾虹、潘天寿,主政央美的徐悲鸿等,以及岭南画派中的高剑父、高奇峰等,亦可作如斯理解。
而在种种流派与风格的背后,上海画家在艺术本体的探索方面都有着极大的成就。以中国画而言,无论是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一脉对于唐宋绘画的追溯,抑或黄宾虹、钱瘦铁、陆俨少、张大壮、程十发等对中国悠久写意艺术的拓展,以及林风眠、关良、刘海粟、程十发融会东西方艺术的探索,无不是卓然大家。
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巨大变化,北京上海两地中国画院的成立与组织对中国画的生态有着极大影响。以上海中国画院2016年建院六十周年文献展为例,呈现的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之初的画家面对当时社会变化的遭遇与态度,无疑让人深思。由于彼时的国家文化战略向苏式美术与宣传类美术倾斜,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艺术家,但同时也出现如郎绍君先生所言的“美术院校外迁,课徒受限,艺术传承出现断层。”
现在看,这个断层虽然存在,但正如岩浆涌动的地下,中国画与文脉的传承在上海一直就从未中断。一方面,上海中国画院开始启动师徒相承制,并专门举行拜师仪式,如陆一飞、邱陶峰分别拜吴湖帆、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吴玉梅拜唐云为师学习花鸟,画院还请张大壮教花鸟,陆俨少、俞子才教山水,来楚生教篆刻……
另一方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不少画家,不少毕业于新式美术学校,学校教育大抵以西画为主体,而在上海美专外迁后导致上海西式美术教育中心的弱化,但反而促进了民间师徒相承方式的发展,一些年轻画家开始顺着自己的本心寻找中国画的发展之路,歪打正着地又寻回了中国画的正脉之路——目前看,上海书画创作的中坚力量,不少在当时都受益于民间师徒相承或雅集问道问学的方式,老一辈的如林曦明之于王个簃、林风眠,刘旦宅之于徐堇侯,1940年代出生的画家中,如萧海春之于黄宾虹的弟子王康乐、顾飞,了庐之于张大壮、关良,吴颐人之于钱瘦铁、钱君匋,周阳高、郑伯萍之于吴湖帆弟子俞子才等……而在美术院校的教育中,潘天寿、陆俨少作为受海派熏染的大家,其中国画教育主张在浙江美院等学校的施展也对中国画的传承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彼时上海中国画的传承起到了反哺的作用,此外,上师大、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等也不容忽视,如至今活跃在上海中国画理论界与创作的不少名家也多有出自这一教育体系。
(三)
相比民国时期海派艺术流派的纷繁与人才的不断出现,由于在五六十年代户籍政策而导致的大量文化移民中断,加上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家文化战略向通俗美术倾斜,上海除了仍拥有一批老画家外,逐渐失去大量补进年轻国画人才资源的优势,这直到上海近十多年在大发展改革人才引进政策才真正出现转变。
 江宏《松谷清音图》
江宏《松谷清音图》在承继中国画文脉的基础上,不少上海画家仍从民国时期遗留的海派风范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指归,并向前探索,试图以坚守传统自身为革新动力——这种探索有时在官方美术机构举办的展览甚至未见其踪,因为一些画家选择的几乎是隐居与不欲人知的方式。其中,有受谢稚柳陈佩秋影响,从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金城而追溯唐宋青绿山水传统的,也有结合自己的性情从黄宾虹齐白石而追溯宋元南宗与“四僧”一脉,也有结合更上古之风进行笔墨探索的……在继承中国画千百年来丰富的笔墨等程式性语言的同时,上海山水画家对于“笔墨当随时代”与笔墨创新的思考一直并未停止——虽然他们也许并未提出“创新”二字:比如,陆俨少在山水画中通过勾云、勾水、大块留白、墨块形成山水画层次,陈佩秋结合域外山水的观察利用叠彩法对青绿山水技法与意境的探索,林曦明对于齐式山水与林风眠风格的借鉴与消化,程十发绘写人物画之余对山水画的低调回归,刘旦宅对山水画与“雁荡画派”的思考实践(虽然刘旦宅的这一探索功未成即抱憾去);而其后,则又有萧海春由当代水墨回归于宋元明清的笔墨传统之中,一些作品结合写生且融入琢玉与西画技法,了庐以文人心性对简笔山水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江宏以行草线条入画结合泼彩而形成的写意山水,卢甫圣借鉴魏晋六朝画对于山水画技法与意境的追寻,即便以研究黄宾虹知名的王中秀或以写评论画人物知名的谢春彦突然抛出一本山水册页与手卷,其率性之笔也颇让人惊异于上海画家的低调与才气……此外,上海书画出版社也是上海书画传帮带的一个基地,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些画家如陈翔、邵琦于此即得益不少。
 陈翔作品
陈翔作品 邵琦《不见茅斋旧隐君》
邵琦《不见茅斋旧隐君》另一方面,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另一批上海本土画家在成长期的七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大开,向往于欧美的现代艺术,或先后走出国门,直接借鉴西方当代艺术,或受其影响,试图从当代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画的创作与定位,这里面一方面有仅仅把水墨作为一种表面的媒介与材料,以至于放弃中国画所有语言包括内在的精神(因展览主题原因,这些画家此次并未列入),另一方面,也有在注重文脉笔墨的同时受林风眠等前辈影响而大胆探索中西融合以谋新之路者,如本次大展选入的杜之韦、何曦、陈九等,除了技法上的探索,也有观念艺术的一面。
 陈琪《雪岱图》
陈琪《雪岱图》 陈九《春水》
陈九《春水》颇有意味的是,部分六十年代出生的画家因受到西式美术教育,对中国文化与笔墨理解不无隔膜,因而热衷于把水墨当作材料以至于放弃中国画的程式语言,而几乎是同时,同样有一批更年轻的画家却自发地在传统的领地进行再一次深翻,沿着前辈以传统自身为革新动力的路径前行。
 顾村言《岱庙汉柏》
顾村言《岱庙汉柏》此次画集收录的出生于七零后的一些画家或皈依唐宋青绿工笔一脉,或醉心于吴门“四王”气韵,或优游于元明山水风范,或以书入画,结合写生,从更大的视野追溯从汉晋至明清、民国的中国画写意传统,并已初见规模与气象,待以时日,必有更加可观处。
 汤哲明作品
汤哲明作品这些画家中,上海真正开放后引入的“新上海人”也占有一定比例——正如郎绍君先生提出从移民变化考察海上艺术的角度,这也是考察十多年来“新上海人”不断涌入上海的背景下重看上海中国画的一个线索,即这些更年轻的画家通过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审视中国画,对中国画的传统与文化精神已有了更自觉的追求与定力。
 邵仄炯《又见家山三》
邵仄炯《又见家山三》无论何时,相比以权力巩固艺术地位的地区,上海画家的群体中对于艺术本体探索的深度与卓然独立的态度似更加明显,江南文脉一直在地下蔓延生根,直到当下。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可以理解何以上海一直会出现极具开放视野的艺术家,但同时不断出现重视文脉笔墨与心灵深度的艺术大家——与一些地区的艺术喧嚣与夸张不同,当下的不少上海艺术家们依然存留着属于江南特有的内敛与矜持,上海艺术界或隐或显仍然尊崇南方文人一直崇尚的书卷气,至少,江湖气太盛在上海是根本无法真正立足的,这也可以说明一些浅薄浮躁的画家在其他地区可以轰动,但在上海,却永远无法被真正认可。
这是上海这片土地经过百年流转而凝固的格调,然而其实更是有底气的——比如,也只有吴湖帆才会有“待五百年后论定”的闲印,也只有黄宾虹才会说出“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能为世所知。”
 庞飞《山外山》
庞飞《山外山》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画界的价值判断体系在当下仍不无紊乱,上海山水画界也并非没有浮躁之气,亦如鲁迅从文学角度辨析京派海派所言的“近官”或“近商”,中国画家的“近官”或“近商”从来就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会有,这是各人的造化与选择,这无可否认——然而,经历过岁月世事的洗礼,有着真正中国文化精神与卓然独立的画家从来不会是“近官”或“近商”的代名词,对于艺术也并不仅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回顾百年来上海山水画求索的真正精神所系,一方面正在于对艺术本体的探索与追求,更在于从不屈服于权力、资本、世俗等种种外在的力量,从不放弃自己的本心,以艺术的形式探索这个民族的心灵深度,呈现对于人生自由与心灵解放的巨大张力。这样的画家在中国画史上虽然从来只是少数,但其力量与影响却是巨大的。
 朱忠民作品
朱忠民作品从这些角度而言,结合“文心雕龙——上海山水画邀请大展”看今后上海山水画在中国艺术版图的份量与深远意义,是没有理由不持更加乐观的态度的。
(作者系《澎湃新闻·艺术版》主编)
——————————
链接:“文心雕龙——上海山水画邀请展”的三大板块:原道,通变,神思
据介绍,此次展览借鉴中国经典古籍《文心雕龙》中的章节,分为“原道”、“通变”、“神思”三大版块。作为上海二三十年来规模较大的山水画大展,这次大展参展画家包括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画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画家,九十岁以上的有多人,年龄最大的97岁,年龄最小的则是出生于80年代的画家,参展作品120多件,其中既有煌煌山水巨制,也有即兴写生之作与见出文人雅兴的山水手卷与册页。这一画展也是一个真实的纪录,三代人的笔墨与心中的家山,不仅是百年来中国山水画跌跌撞撞回环往复一路走来的鲜活见证,也承载了中国画前辈大家到当代上海画家对中国画与中国文化的诸多思考与期望。
 谢春彦作品
谢春彦作品展览的第一部分“原道”在于这次展览也试图回答中国画该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画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目标,正在观照与解决天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生命中最鲜活的所在,中国绘画之所以呈现出与西方绘画完全不同的路径,也正在于从一开始就是致力于“道”的认知,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或谓一种诗性的探寻,同样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并不仅仅是技之层面的话题——当然,技却又是一个基础。“原道”部分的作品包括九旬书画大家陈佩秋的《 高山春水》、 《树接青溪图轴》 ,林曦明的 《 湖上渔歌 》,以及丁立人的《天台胜景》,谢春彦 《山水杂写(四联画)》 ,萧海春《山阴道上》,江宏《石壁长松》 、阮荣春 《山水清韵》 ,乐震文《山冻不流云》、朱敏 《苍山半云雨》,邵琦《春气动百草》、陈志雄《太行》、汤哲明《羊角洞天》、朱忠民《春和景明》、俞丰 《云谷奇松》、邵仄炯 《快雪时晴》等。
 林矗作品
林矗作品第二部分“通变”主要呈现上海山水画创作在开拓新境与吸收西方文明方面,显示出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中有试图以坚守传统自身为革新动力,结合古风进行笔墨探索的,也有在山水画中直接借鉴西方当代艺术者,也有受前辈影响大胆探索中西融合以谋新之路者。
 乐震文作品
乐震文作品 张弛作品
张弛作品包括卢甫圣 《终南》,张雷平的《水墨山田(三联〕》,杜之韦的 《大峡谷》、陈琪《阿尔卑斯山雪景》、张弛 《和光同尘》,陈九《水系列》、乐坚《山水》,何曦《标本·倪瓒》、林矗《太行山》、毛冬华《外滩》、庞飞《山外山》等。
 毛冬华作品
毛冬华作品第三部分“神思”主要展出有着文人心性的画作,宋元以来中国山水画多求文人气,呈现的是中国书画与心性结合的一个高度,董其昌云:“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回顾百年来上海山水画求索的真正精神所系,一方面正在于对艺术本体的探索与追求,更在于从不屈服于种种外在的力量,从不放弃自己的本心,以艺术的形式“神思”,探索这个民族的心灵深度,呈现对于人生自由与心灵解放的巨大张力与境界。包括知名画家了庐的《苍龙岭》、 《太湖烟波》,车鹏飞《孟浩然诗意图》、陈翔《柳阴絮语》,余启平《瓶中山水》,吴林田《写意山水》,顾村言《岱庙汉柏》、牛孝杰《空山无人》等。
 吴林田山水
吴林田山水来源: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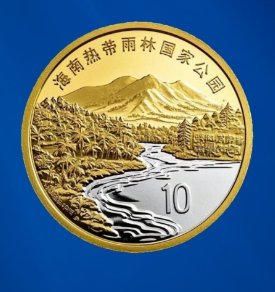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