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满足经济发展的对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所谓的最优金融结构是与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相关联的。而不同的金融结构有着不同的风险结构,金融风险的分布范围、类型、相关关系和风险量级都有所不同。不适应本国本阶段金融结构的监管模式监管效率低下,会制约金融发展和创新;而适应与金融结构的监管模式监管效率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甚至引导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创新。
一、美国的“多元监管者”或“部门监管”模式
美国的金融监管是在联邦层面和州层面同时存在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在“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中,美国于1933年通过了银行法案,也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区分为特定的部门,银行、证券和保险彼此分割,相互独立,也分别由彼此独立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为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和全球化浪潮,美国于1999年通过《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模糊了分业监管结构下不同金融市场的边界,允许成立“金融持股公司”或“银行持股公司”,这类公司能够从事包括保险和证券在内的任何金融活动,是美国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标志。
然而,1999年的金融现代化法案并没有完全废除1933年的银行法案建立的分业监管体系,也没有在实际中建立起一个体现功能监管的监管结构,功能监管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结果是,美国的金融监管更像一个机构型监管和功能型监管的混合体。但监管当局根据金融部门 (无论基于金融机构还是基于金融行为)被分割开来,都有多个监管者,因而可被成为“多元监管者”或者“部门监管”模式。
随着美国金融证券化的发展和金融风险结构的演变,这种部门监管模式越来越体现出与金融结构的不匹配。针对于此,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尽管这份改革法案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固有缺陷,但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 “多元监管者”或者“部门监管”的模式。
二、英国的“单一监管者”或“综合监管”模式
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美国模式的另一极端――只有一个权力极大、几乎全能的监管者――金融服务局。因而也称为“单一监管者”或“综合监管”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传统的监管体系也是多元化体制,不同的监管机构有不同的监管分工。然而随着本国金融业的持续变革,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相互渗透、日益融合,原来的多元化监管体系显示出职责不清晰且监管效率低下的缺点。
2000年英国议会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金融服务监管局正式成立,将之前由英国九个金融监管机构分担的监管职能聚于一身。金融服务监管局从而成为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金融管理者:它不仅监管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业务,而且负责各类审慎监管和业务行为监管。为了应对本轮金融危机,2009年的银行业法案又增加了英格兰银行“保持金融稳定”的法定目标,以防止特定领域的问题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三、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者”或“基于目标的监管”模式
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居于多元和一元之间的一种模式。1997年的Wallis报告检查了澳大利亚金融创新和现代化的结果,认为传统的基于部门的金融监管已经不再有效,建议一个由两个监管者构成的监管框架。
其一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负责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务行为的监管。它具有了多个角色:公司监管者,金融市场监管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者。其二是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整个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保证所有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由于澳大利亚监管机构由以上两个单独的具有不同权限的监管者组成,它们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业务行为监管,所以可形象地称之为“双峰监管”或者“基于目标的监管”模式。
四、主要监管模式的演变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从全球金融结果演变与金融监管体制的互动关系看,中国需要根据自身金融结构的发展阶段及其风险结构特征,选择适合于中国的监管结构和变革方向。如何安排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路径,需要基于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充分论证和成本收益分析。当前,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分业经营的金融结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特征,和金融行业之间风险结构相对隔离的现状,中国可以更多参考美国基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功能的多元监管者模式。同时,重点关注大型金融集团的监管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集团。这些集团往往规模巨大,而且经营横跨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不同行业,对整个金融体系会造成严重的系统性影响。其次,应该创造条件,针对金融创新在交叉领域不断涌现的现实,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的综合性金融监管组织,将横跨不同市场的相关监管者(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整合在一起,加强合作、共享信息并填补监管空白。
从中长期的演进趋势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发展,金融部门之间的界线并不再泾渭分明,金融风险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传导更加隐蔽、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而未来中国的监管结构更多要考虑澳大利亚的较为一致化的基于目标的“双峰监管者”模式,或者监管整合更高的英国的完全综合化的 “单一监管者”模式。这也为中国金融监管提出了长远的改革方向。(作者 巴曙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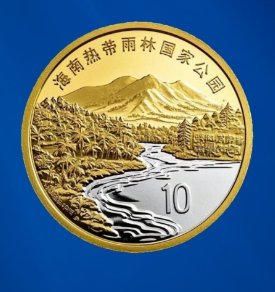






27